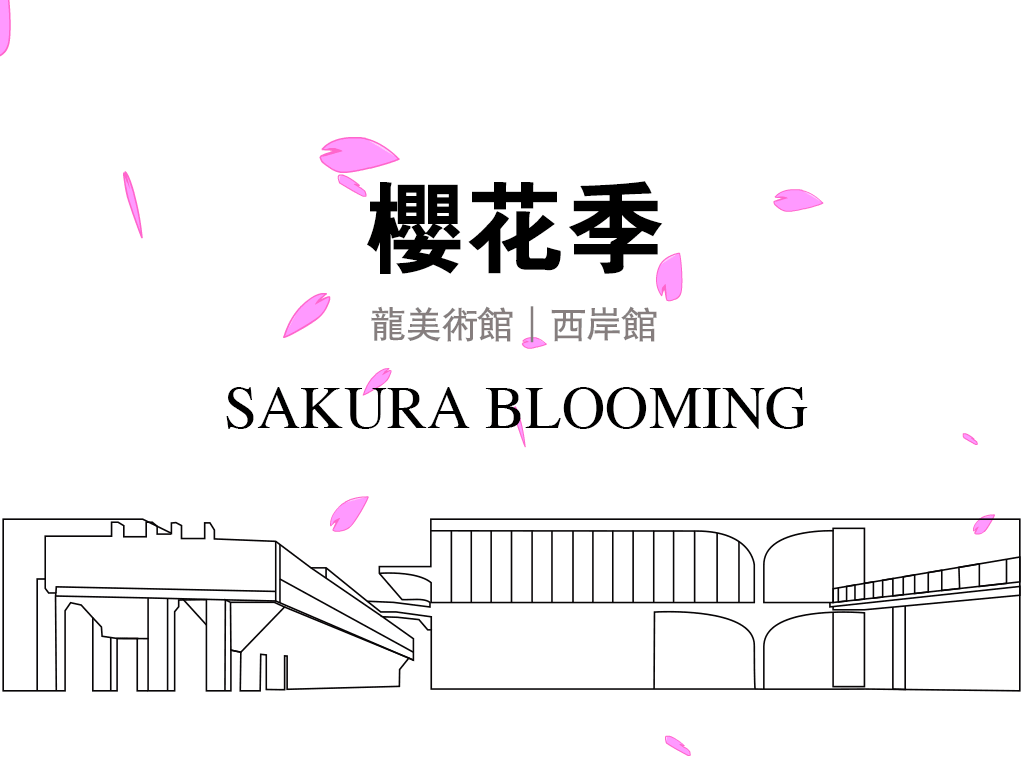“伤痕美术”与何多苓的诗意伤痕
“伤痕美术”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出现的美术现象。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年代,有人说这是一个“神”时代的结束和一个“人”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们有着所有年轻人特有的躁动和突破主流的意识。当压抑与空虚连绵不绝,那些内心的呐喊便越丰盈,也极易出现社会思潮。
对于苦难的揭露,当“伤痕文学”以悲剧的力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后,受其影响,在美术界也出现了对进行批判和反思的“伤痕美术”。和伤痕文学从原先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一样,“伤痕美术”的作品也从表现英雄转变为描绘大时代里普通人的现实命运。政治,社会形态的转变促进了审美意识的转变,艺术家们将现代艺术语言和观念融入到艺术创作中。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意识到,应该把对国家符号的崇拜转向对于普罗大众的关注,因为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是无与伦比的。

陈丛林《1968年某月某日雪》1979
“伤痕美术”无意粉饰,以反思和批判的基调为主要特征,以写实的手法再现,摆脱了时期的风格,色调开始变得冷而灰,饱含了伤感的人道主义。“伤痕美术”的代表人物有何多苓,高小华,程从林,周春芽,张晓刚,罗中立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美术作品有刘宇廉、陈宜明、李斌三人合作的《伤痕》、《枫》;高小华的《为什么》、《赶火车》;罗中立的《父亲》,程丛林的《1968年某月某日•雪》以及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

高小华《为什么》1978年

罗中立《父亲》1980年



刘宇廉、陈宜明、李斌三人合作的《伤痕》1978至1979年 部分

刘宇廉、陈宜明、李斌三人合作的《枫》1978至1979年 部分
《春风已经苏醒》作为何多苓艺术生涯的转折点,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这幅作品看来细腻而忧伤,看来是非常平凡的乡村场景,但是正是大自然赐予的生命和春天的生机将少女、牛和狗联系在一起,似乎可以从中窥到人与自然的神秘联系。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追寻更像是一种对于自己想象中的西方文化的追寻。不管是安德鲁•怀斯的绘画还是杰弗逊的诗歌,都在何多苓的创作情感上有着影响。何多苓极其重视绘画语言的精确性,他把意象融入画面,给人一种精神张力和抒情韵味,从另一个美学视角开启了中国写实主义绘画。优秀的作品都具有“永恒性”,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

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1982年
“我的早期作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伤痕。但你可以把伤痕看作是诗意的一种,那里面包含的不是苦难,而是美。”(《何多苓:从诗意到恐怖》)
和其他诸如《父亲》、《为什么》中表现的肉体与精神的现实“伤痕”不同,何多苓的“伤痕”似乎和现实社会并无关联,更多的像是一种形而上的忧愁,他的作品里有很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对于自由的追寻如此纯粹。

何多苓《青春》1984年
“(绘画)是一个人可能独立进行并完成的行为,仍然可以保持沉默、优雅、不带有攻击性和排他性。不需要策划、方案、审批、设施、宣传系列自虐的过程,从头到尾只需要一个人。”(《何多苓自述》)
何多苓的艺术鲜明地指向艺术本身,他重视纯粹地绘画语言,他认为诗意是必须隐含在其中。可以说他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画家,身为一个“题材型”的画家,让他似乎也脱离了现实的重压。
伤痕美术的艺术家们开始关注内心的需求,回归于现实的平凡,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上,是一种对于人性的回归,与此同时也助长了乡土现实主义绘画的萌芽。